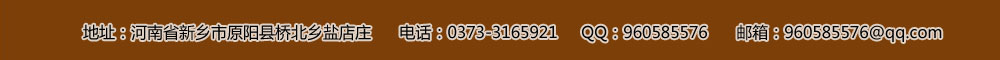手术应激后低蛋白血症启因及治疗的最新进展
本文原载于《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年第3期
肝胆管、胰头癌等大手术患者术后1周内常出现严重低蛋白血症[1]。白蛋白是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的主要成分,具有调节组织与血管之间水分的动态平衡、运载体内血红素、激素和脂肪酸及抗氧化等作用。因此,低蛋白血症会引起肺间质水肿、肠道壁水肿、术后吻合口瘘、伤口裂开等并发症,甚至增加病死率。研究表明,危重患者血浆白蛋白水平下降提示预后不良[2]。深入研讨大手术后低蛋白血症的成因及寻找精准的治疗方法,可为临床术后治疗提供依据。
1
手术后应激导致低蛋白血症发生的机制(图1)
1.1 内分泌代谢因素:
手术时,创伤信号从损伤部位通过感觉传入神经纤维向中枢神经系统传导。神经冲动传达到中枢神经系统后,兴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HPA),使自主神经系统活性增强,释放各种应激激素,儿茶酚胺释放入血;此外,促皮质激素释放激素、β-内啡肽、β-色胺酸羟化酶、生长激素、甲状腺激素、皮质醇、胰高血糖素增加,而以胰岛素等为代表的合成激素分泌减少,即内分泌代谢反应[3]。手术后应激内分泌代谢的基本特征是分解激素水平升高,合成激素水平降低,造成高代谢状态,引起血糖升高、脂肪分解和蛋白质消耗等,导致低蛋白血症。
1.2 炎性因子的作用:
研究表明,尽管负性急性期蛋白半衰期各不相同(白蛋白18d,转铁蛋白8d,前白蛋白2d)[4],但其术后血浆水平迅速降低,且降低速度相同,这意味着术后低蛋白血症的发生主要是白蛋白透过血管壁进入组织间隙的缘故,而不是白蛋白分解代谢加快所致[5]。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的白蛋白约以每小时5%的速度移动到血管外,然后由毛细淋巴管重吸收回到血液循环中;但在严重创伤等严重病理状态下,血管内皮细胞受损,血管通透性增加,白蛋白进入血管外组织间隙的速度也显著加快,超过了毛细淋巴管的重吸收能力,造成血中白蛋白降低[6]。
手术创伤激活全身炎症反应,炎性介质使微血管内皮间隙开放,导致微血管白蛋白渗漏[7]。急性炎症期形成时,内皮间隙迅速形成并随介质的量的增加而增加。内皮间隙与微血管系统中渗漏位点的分布相匹配,内皮细胞连接间隙开放后,白蛋白不需要依赖能量的膜运动和囊泡穿梭运动即可通过内皮间隙。因此,目前认为内皮间隙是炎症时微血管渗漏的"位点"。在大手术、创伤等应激条件刺激下,机体可产生大量炎性介质,且其水平与手术创伤大小呈正相关[8]。
1.2.1 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
腹部大手术后,各种细胞因子发生复杂的连锁反应,TNF-α在此环节中具有核心作用[9]。TNF-α是一种炎性细胞因子,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同时又是一种内源性致热源,一方面可以直接参与炎症反应引起发热,诱导细胞凋亡等;另一方面可以与内皮细胞结合,增加过氧化物阴离子产生,刺激细胞脱颗粒,从而促进内皮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IL-8、IL-1)和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等炎性因子。此外,TNF-α还能激活单核/巨噬细胞及白细胞,促使其释放IL-1、IL-8等,使炎症放大,因此TNF-α又被称为"广谱炎性介质"[10]。还有研究显示,炎性因子与急性心肌梗死发生发展有关[11]。经TNF-α处理后,体外培养的血管内皮细胞发生重叠、激动蛋白丝重新排列及纤维连接蛋白丢失等形态学改变,高浓度的TNF-α则能对血管内皮细胞产生直接毒性作用[12]。TNF-α还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损伤血管内皮细胞,使微血管的通透性发生改变。
1.2.2 IL-6:
IL-6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T淋巴细胞和纤维母细胞合成。IL-6是参与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的重要细胞因子之一,是机体对感染和组织损伤发生反应的主要介质。一方面,IL-6能激活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抑制白蛋白mRNA表达[13]等;另一方面,IL-6能抑制TNF-α、IL-1等的受体。因此,IL-6同时具有促炎和抗炎双重效应,是组织损伤的标志,也是引发免疫反应的轴心,在炎症调控中处于枢纽位置。Maruo等[14]通过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标记的白蛋白观察IL-6对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的影响,发现IL-6可通过改变内皮细胞的形状和微丝重排来诱导急性期蛋白的合成,催化和放大炎症反应,同时其直接毒性作用可增加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
1.2.3 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
ICAM-1是一种单链跨膜糖蛋白,由细胞外区、疏水的跨膜区和较短的胞质区组成。细胞外区可以作为配基与白细胞表面表达的整合素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LFA-1,CD11a/CD18)和Mac-1(CD11b/CD18)结合,介导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牢固黏附及跨膜迁移。在正常生理条件下,ICAM-1的表达及活化都受到严格的调控,只有在IL-1、TNF-α、脂多糖(LPS)等作用下,ICAM-1表达才会上调并与配体结合,使多种途径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激活,导致细胞骨架蛋白重组,造成细胞形态变化以及细胞的增生、分化、调亡、细胞因子生成等。有研究报道,内皮细胞膜上的ICAM-1与中性粒细胞(PMN)膜上的CD11b/CD18互为配体或受体,二者结合后形成新的通道,氧自由基中的蛋白酶等物质可经过这些通道直接进入内皮细胞,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导致血管通透性增加[15];另有研究表明,CD11b/CD18与ICAM-1结合后,ICAM-1可引起内皮细胞收缩,从而使细胞间隙增大[16]。
1.2.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
VEGF又称血管通透性因子(VPF),是血管生成的主要调控因子。VEGF通过与内皮细胞表面特异性抗体结合而发挥其生物学特性,同时也是血管内水分子和蛋白通透的重要调节因子。VEGF增加血管通透性的作用是多途径的,涉及复杂的细胞及分子机制。研究表明,VEGF增加血管通透性的机制可能涉及到细胞与细胞间的相互作用,认为VEGF增加生物分子从内皮细胞周围通过与钙黏着蛋白(VE-cadherin)、链蛋白(α-catenin、β-catenin)和连环蛋白P构建方式等细胞间黏附蛋白的改变有关,这些细胞间黏附蛋白在细胞内相互连接并最终与细胞骨架蛋白相连,起到稳定细胞的作用[17];还有报道显示VEGF能直接促进内皮细胞"窗口"的形成[18]。
1.2.5 IL-2:
IL-2主要由活化的CD4+辅助性T细胞1(Th1)产生,有广泛的生物活性,通过增加整联蛋白及CD11B/CD18的表达来激活白细胞,也可以通过刺激淋巴因子来激活杀伤细胞,扰乱细胞间连接和基底膜基质,从而增加血管通透性。
1.2.6 组胺(HIS):
HIS由组氨酸脱羧形成,常贮存于组织肥大细胞。HIS是体内重要的化学递质,机体受到某种刺激引发抗原-抗体反应时,导致肥大细胞的细胞膜通透性改变,释放HIS,与HIS受体作用产生病理生理效应。Dvorak和Feng[19]在HIS和5-羟色胺诱导血管渗透性研究的动物模型中也发现,HIS和5-羟色胺主要通过增加囊液泡细胞器这一渗漏位点开放来增加血管通透性。在大手术或严重创伤初期,机体产生IL-6、TNF-α等大量炎性介质,一方面与炎性细胞相互作用;另一方面,高浓度的IL-6及TNF-α可激活细胞因子发生级联反应,诱发IL-2、ICAM-1、VEGF、HIS等炎性介质释放。动物实验结果显示,术后炎性介质浓度均高于术前,说明手术创伤引起了炎性介质的释放[20]。
因此,如何保证血管内皮细胞和多糖包被的完整性,如何控制炎症以降低炎性因子对通透性的影响,使白蛋白停留在血管中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将成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
2
手术后低蛋白血症的防治(图1)
血浆白蛋白对机体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低蛋白血症可影响机体创伤的愈合恢复。组织间液和血浆之间的液体移动主要取决于毛细血管内外的胶体渗透压,血浆白蛋白作为胶体渗透压的决定性构成,其水平低于正常范围会导致血管内胶体渗透压明显低于静水压,血管内液体外渗并蓄积在组织间隙,出现低血容量性水肿。水肿直接影响组织的愈合,使伤口裂开,发生吻合口瘘,造成脓毒症,影响预后,甚至危及生命。因此,防治手术后低蛋白血症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事实上,目前临床对于术后低蛋白血症并没有系统有效的治疗方案,治疗原则也以控制生化指标为目的。因此,探讨手术后低蛋白血症的发生机制,并针对其发生机制指导临床控制和治疗才是最重要的。
2.1 补充人血白蛋白(HSA)与肠内营养支持:
尽管低蛋白血症是外科手术常见并发症,但也因疾病、术式而异。目前临床对于手术后低蛋白血症最常用的处理方法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症治疗,即输入HSA。作为天然胶体溶液,HSA可与晶体溶液联合用于液体复苏,改善机体血容量不足,同时也可用于纠正低蛋白血症。研究表明,早期给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外源性白蛋白输注,可有效维持患者血清白蛋白水平,遏制蛋白从肺毛细血管漏出[21]。从检索到的文献看,除肝脏手术相关研究外,目前HSA用于腹部外科手术治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腹部血管手术和胃肠道外科手术,但对于应用HSA的结果存在分歧[22]。有研究表明,对于白蛋白≤20g/L者,给予白蛋白可能降低其28d病死率;但同时发现,对于白蛋白20g/L者,给予白蛋白却无影响。因而推测,白蛋白仅对伴有严重低蛋白血症的脓毒症患者有益[23]。还有研究表明,应用HSA尽管可以使生化指标好转,但对于预后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24],甚至会增加病死率[25]。因此,不能盲目使用HSA,HSA在增加血容量和维持血浆胶体渗透压、运输小分子物质及解毒、营养供给方面有明确适应证,临床应用HSA应把握适应证,避免滥用,促进规范用药,如失血性休克、烧伤、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等[26]。此外,肠内营养也是临床上的常用手段。研究表明,围手术期尽早行肠内营养可以提高肠道耐受力,增强免疫功能,改善患者营养状况[27];同时可使血清白蛋白浓度明显升高,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时间减少,改善患者预后[28]。肠内营养对改善危重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病死率具有明显的优势[29]。与肠外营养相比,肠内营养危重患者的感染发生率和病死率明显降低[23]。而针对术后低蛋白血症,与输注外源性HSA相比,肠内营养支持更安全、经济,但这也只是在术后已经出现低蛋白血症的补救措施,并不能预防术后低蛋白血症。
2.2 采用微创手术减少组织损伤:
外科手术创伤是引发应激反应、刺激炎性因子释放的主要原因,采用微创手术减轻组织损伤可有效防治术后低蛋白血症。目前,微创手术不断更新发展,尤其是腹部外科手术[30],腹腔镜已成为主流。有研究显示:与传统手术治疗比较,微创手术能达到相同的治疗效果[31],且术后并发症明显减少[32]。因此,选择适当的手术方式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术后低蛋白血症的发生。
2.3 控制应激反应
2.3.1 不同的麻醉方式对应激反应有着不同的影响:
在全凭静脉全麻的基础上联合硬膜外麻醉,通过抑制刺激的上行传导,减少儿茶酚胺释放,抑制HPA轴兴奋,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发挥减缓心率、降低血压的作用,比单纯全身麻醉可更有效地减轻应激反应[33]。还有研究显示,与气管插管静脉麻醉和吸入麻醉相比,连续硬膜外自控镇痛联合全身麻醉可减轻围手术期应激反应[34]。在手术结束时给予切口局部浸润麻醉也可以减轻手术损伤对患者的后续刺激。因此,应用更完善的麻醉方式尽可能减轻应激反应,可考虑作为预防术后低蛋白血症的方法。
2.3.2 适当用药也可减轻应激反应:
阿片类药物可调节应激激素的分泌和血流动力学反应,同时不会对心血管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常用来控制应激反应。另外,有研究显示,七氟醚联合瑞芬太尼用于腹腔镜子宫切除术麻醉时可很好地抑制麻醉过程引起的应激反应[35]。
2.4 炎症反应的调控
2.4.1 镇痛治疗:
创伤后疼痛是创伤应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启动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这一复杂病理生理反应过程的主要始动因素之一,可导致大量细胞因子释放,引起机体内环境失衡等。故创伤后镇痛可减少细胞因子释放,缓解炎症反应,有研究已初步证实,创伤后镇痛能有效调节患者的皮质激素和细胞因子的释放[36]。
2.4.2 药物调控:
咪达唑仑、丙泊酚可降低脑损伤术后应激反应过程中β-促脂激素C末端31肽(β-EP)、热休克蛋白70(HSP70)、血乳酸、血糖等应激指标水平[37]。持续泵注右美托咪定联合常规静吸复合麻醉有助于稳定血流动力学,缓解围手术期应激反应,减少炎性因子释放,维持手术过程中生命体征相对稳定[38]。
磷酸二酯酶4抑制剂(PDE4)能通过降低TNF-α、弹性蛋白酶血浆浓度及PMN内CD11b过度表达,有效减轻心血管急救(ECC)引起的炎症反应。TNF-α和IL-1β在炎症反应初始阶段具有重要作用,能诱导PMN和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化,参与炎症反应。PDE4能通过增加细胞内环磷酸腺苷(cAMP)水平有效抑制TNF-α表达[39]。
研究显示,术后使用羟乙基淀粉可降低IL-6、TNF-α、IL-2、ICAM-1、VEGF水平,有效扩大血管内血浆容量及血管内胶体渗透压,使促炎炎性介质释放减少,内皮细胞活性降低,防止PMN黏附,降低血管通透性,减少微循环损伤,从而保护微循环,其相对分子质量大小适中,可附着于增大的"孔道"或内皮细胞间隙封堵渗漏[40]。
前列腺素E1(PGE1)可能通过抑制内皮细胞表达黏附分子,减少PMN与血管内皮细胞的黏附,抑制白细胞和血小板的聚集,从而减轻炎症反应;PGE1还可减少体外循环引起的PMN和血小板在肺内聚集及血管内皮细胞激活,缓解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抑制全身炎症反应,减轻肺损伤[41]。
2.4.3 激素治疗:
糖皮质激素能减轻应激时的炎症反应[42],缓解早期炎症过程,如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白细胞迁移及随后的毛细血管增生和胶原蛋白沉积,抑制炎性因子释放,提高抗炎细胞因子IL-10水平[43];还能抑制LPS诱导的单核细胞分泌TNF-α,降低核转录因子-κB(NF-κB)与DNA结合能力,下调细胞因子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表达,通过保护NF-κB抑制因子(IκB)抑制NF-κB的活性[44]。
因此,可考虑在手术过程中应用上述药物调控炎症反应,如术中给予患者少量激素和PDE4一直TNF-α释放,从炎症反应发生的起始阶段进行控制,减轻炎症反映轻度,预防术后低蛋白血症的发生。以上治疗方法仅单纯针对术后低蛋白血症发生机制的理论上的措施,是否有效或对预后是否有影响还需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
3
展望
尽管对手术后各类细胞因子水平的改变进行了许多研究,也已证明大量细胞因子参与了创伤后炎症反应和低蛋白血症的发生过程,但具体机制尚不明确,且创伤后炎症反应体系极其复杂,尚不能全面阐明相关细胞因子在炎症反应中的作用机制。单一控制某方面因素对于控制创伤后炎症反应和术后低蛋白血症略显苍白无力,因此,从炎症反应的源头(即创伤后应激反应)进行调控显得尤为重要,但仍有待更为深入全面的临床研究。在外科手术过程中,能对患者内环境稳态进行干预的只有麻醉医师,因此术中干预,从源头上减少患者的创伤,也是我们以后努力的目标。